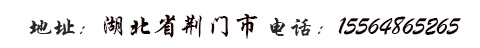曾业英蔡锷与小凤仙历史真实与民间传说
|
早期白癜风能治好吗 http://pf.39.net/bdfyy/tslf/181207/6698604.html 提要:蔡锷任职袁世凯北京中央政府期间,结识了年仅十六七岁的风尘女子小凤仙。小凤仙本不是“名妓”,更非助蔡出京的“侠妓”,这些“美誉”皆源于为反袁称帝献出了年轻生命的蔡锷的英名。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只是他返回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谋略中的一环,不存在所谓“相恋”的问题。其京津脱险,经历了出京和离津两个步骤,出京并未逾越袁世凯所允许的范围,唯有离津才称得上“潜逃”。小凤仙对蔡锷的成功返滇起了一定的掩护作用,却是她始料不及的,但其祭奠蔡锷的行为理当受到尊重。历史研究不能盲目随“后现代”理论起舞,应高度重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工作。 蔡锷与小凤仙 ——兼谈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问题作者 曾业英 一、缘起 首先要说明一下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因为比较严肃的历史论著似乎都不愿深谈或者回避这个问题。 至年蔡锷任职袁世凯北京中央政府期间,结识了南城陕西巷云吉班一位自称“小凤仙”的风尘女子。这在那个年代本是一件无足挂齿的寻常小事,据时人说:“北人视狎妓为极平常之事,父子兄弟可以同往,不过借之以销长晷,未必尽有醉翁之意,故人人趋之若鹜。”但因这事正好发生在蔡锷京津脱险,海天万里,间关入滇,发动反袁称帝的惊天大事之前,于是便成了各种社会媒体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 就我所接触的资料来看,蔡锷这时确与小凤仙有所交往,而且还有迹象表明,当时无论民间还是官场,对于此事均有传闻。不过,在蔡锷逝世以前,却没有发现关于此事的任何直接记载,甚至连“小凤仙”三个字也不见于各种报刊,仅仅偶尔见到事态明朗化以后,才能理解的零星半点暗示性记载而已。如与蔡锷暗中有联系的欧事研究会成员年10月10日创办的、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上海《中华新报》,就曾在蔡锷逝世以前含糊其词地报道过蔡锷是“变服乘骡车出京”的。稍后,《香港时报》也在一篇时评中提及:蔡锷终于“天相豫州,犹能脱离曹阿瞒之圈套,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吾为蔡氏个人庆,吾为吾党前途贺也。雪巾车之耻,鞭平王之尸,勖哉。”两则报道都没有直接说出小凤仙的名字。据蔡锷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哈汉章后来说,前者是他和刘成禺、张绍曾、丁槐等人在蔡锷离京后为洗刷他们与此事有关的嫌疑,故意“以小凤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松坡”,向袁世凯政府报告的假消息。如无哈汉章这事后的说明,后人很难明白这两则报道的真正含义,更难以知晓后者所云“巾车之耻”,实际指的也是上述《中华新报》所报道的假消息。所谓“巾车”,就是“有车衣遮盖的车子”,暗指蔡锷当日离京乘坐的是小凤仙的骡车。 但是,自年11月8日蔡锷逝世以后,小凤仙的名字和形象便开始频繁出现在当时的报刊和戏剧舞台上了,并由此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个人迄今所见,在报刊上第一次明确提到小凤仙三个字及其与蔡锷关系的文章,是署名戒甫的作者撰写的《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它发表在蔡锷逝世后的第四天,即年11月12日《长沙日报》的《文艺丛刊》上;在戏剧舞台上第一部涉及蔡锷与小凤仙关系的剧目《再造共和之大伟人蔡锷》,也是年11月12日这一天,在上海《申报》刊出民鸣社的大幅广告,说“十七夜准演双出好戏,《再造共和之大伟人蔡锷》”,其广告词曰:“共和民国得蔡先生而更生,洪宪皇帝为蔡先生而竟死,凡我国民方冀先生身任艰巨,利民福国,不料先生从此去矣,痛哉。本社因即择先生如何反对帝制,如何寄情声色,如何摆脱侦探,如何出险起义,如何被刺不成,如何血战入川,如何再造共和,一一演诸舞台之上。我人〔国〕之人痛先生之死,若人人见蔡先生之事,而人人志先生之志,民国不死,则蔡先生虽死犹生,得不死矣,可不观乎?”紧随其后,民兴社也预告“念一(二十一日)晚准演双出好戏《蔡松坡》”,表示会“将蔡先生在京如何被帝制派监视,如何遣眷脱身,如何入滇举义,如何得病,一一演将出来”。而笑舞台则推出新编歌剧《筱凤仙哭祭蔡锷》,说“筱凤仙与蔡锷究有何等关系,筱凤仙何以哭祭蔡锷,恐知之者甚鲜,本舞台访得实情,编成斯剧……定于(十二月)十一夜开演。”蔡锷家乡湖南新剧社也不甘落后,随即于《长沙日报》刊出广告,说准于12月16日在长沙育婴街上演“政治新剧《蔡松坡》”,剧中人物包括袁世凯、袁克定、蔡锷、唐继尧、小凤仙、小凤仙的母亲、云吉班主等数十人。小凤仙的名字就是从这时起开始出现在各地戏剧舞台和报刊媒体上的。而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能如此神速搬上舞台,也说明他们的交往,早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否则,何能在蔡锷去世仅仅四天,至多也不过一个月,就写出剧本,完成排练,公开上演呢? 蔡锷的逝世,揭开了他与小凤仙话题的历史序幕,此后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文艺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依据新的价值观,重提他们这段往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人以《英雄美人》为题再次将其搬上舞台。年,又有人写就三幕历史剧《袁世凯》,述及蔡锷如何逃出北京。年代以后,我国内地虽一度失声,而台港澳地区却热度不减,年香港推出电影《小凤仙》,饰演小凤仙的李丽华一炮打响,成了耀眼的电影明星。年10月,大陆在改革开放中隆重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拍成电影《知音》,在全国各地上映,风靡一时,扮演蔡锷的王心刚还因此荣获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与此同时,以此为题材的各类戏剧节目,如话剧《一代风流》、同名京剧与越剧《蔡锷与小凤仙》、其他剧种《大将军与小凤仙》,等等,也在各地纷纷上演。稍后,刘晓庆又集资拍摄了由其亲自饰演小凤仙的电视连续剧《逃之恋》,长达30集。这些戏剧影视节目,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和感染力量,不但使蔡锷的英名重放光彩,也使小凤仙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以致时至今日,仍有众多蔡锷“粉丝”,对这一历史话题津津乐道,谈论不休。打开Google(谷歌)网页,输入“蔡锷与小凤仙”6字,竟可搜寻到数万条相关信息。学术界的状况似较影视戏剧界略显寂寞,检视当今各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如《辛亥革命史》《中华民国史》等,对蔡锷与小凤仙这桩历史公案几无只字提及。但也有多种离不开这一话题的论著问世,仅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有多家出版社推出《蔡锷传》,并首次出版了专题著作《护国运动史》,至于相关文章就更多了,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为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知音》和戏剧之余,能观其戏而知其人,“就历史写了《小凤仙其人》”、《再谈小凤仙》两文,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这些戏剧影视节目和学术论著意在告诉人们什么?娱乐之外还有没有共同的思想指向?除少数学术论著对个别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的讨论外,多数舆论在主要问题上的认识似已取得一致,那就是小凤仙是“爱国名妓”,云南护国起义的“幕后人物”,蔡锷“最后靠了小凤仙掩护的力量,终究脱离藩笼”,“从北京到了……云南”,论起小凤仙“对于国家的功勋”,实在不下于当时的蔡锷,堪称“造时势的巾帼英雄”。对于蔡锷与小凤仙的关系,则普遍认为他们的“相恋”,“并非乌有,确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的一则佳话,富有传奇色彩”。经过众多戏剧影视节目的渲染,这些基本看法更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几乎成了社会的共识,以为这就是蔡锷和小凤仙的真实历史。 然而,这些共识有可靠的事实根据吗?历史的真相是这样吗?小凤仙和蔡锷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她掩护蔡锷脱险京津的吗?既然蔡锷与小凤仙一事历来是社会的热门话题,近年更是被互联网炒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那么,作为历史研究者便不能无动于衷,一味三缄其口,采取回避态度,或者模棱两可,搪塞了事,而应努力追求历史的真实,对其做出符合或者接近历史真相的解释,否则,任凭那些似是而非的所谓“社会共识”不胫而走,久而久之,就会为某些好走偏锋,轻视有案可稽的文献资料,片面强调应从“历史传闻”中寻找“历史真相”的所谓“创新”高手提供更多的依据,使这桩历史公案成为更加离奇复杂、难以破解的历史之谜。这是我所以步人后尘,也来凑个热闹,谈谈蔡锷与小凤仙这个热门话题中的是是非非的主要原因。需要说明的是戏剧影视作品并不是历史著作,作为艺术自有其追求票房价值,吸引观众眼球,进行虚构、加工、美化的理由,本文对此不予置评,仅从历史学求真求实角度,对蔡锷与小凤仙这一话题作一探求,权当抛砖引玉的个人意见,呈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二、小凤仙的身世 小凤仙这个名字,今天虽已家喻户晓,但人们对她的了解并不多,直到年10月,陈旭麓写了《小凤仙其人》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经过多种媒体的传播,才使更多的人有了如下的印象:(1)“她是杭州旗籍武官的女儿”;(2)她在北京云吉班时的年龄,“当是一个17至19岁的姑娘”;(3)“她通文字,能阅书报,这是她比一般妓女较有身价的地方”。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可信度如何,还有什么新情况,并未深入探究过。陈旭麓这三个推论,基本来源于地理学家、佛学家张相文《南园丛稿》中的《小凤仙传》和曾孟朴之子曾虚白所撰《曾孟朴年谱》。有学者指出陈旭麓所据两种“史料可以引用”,理由是张相文《小凤仙传》发表时间“最早,出版于一九一八年”,张相文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绝非‘稗官者流’”。而曾虚白则为“孟朴公之哲嗣,子写父传,应不会作假”。况且“著名报人陶菊隐也承认《曾谱》为‘着实之笔’……所以,三者互证,可以结论”。 小凤仙 这位学者的史料辨伪意识值得赞赏,但认为依据上述史料就可以下“结论”了,则不敢完全苟同。以最早的史料作为选用标准当然有一定道理,遗憾的是他未对张相文的《小凤仙传》是否真是发表“最早”,作进一步的调查,仅仅因它发表于年,便轻率宣布为“最早”的。实际上此前的记载多了去了。据我查考,张文其实来源于江苏毗陵(今武进)早期鸳鸯蝴蝶派著名作家李定夷的《英雄儿女各千秋》,而李文又来源于前述署名戒甫的《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一文,请看三文所介绍的小凤仙的身世何其一致。 张相文之文说: 小凤仙,钱塘人。父某清季为武官,落职后,贫不能自活,携家卖饼上海。久之,益困,遂质凤仙于妓寮,以凤仙齿稚,英警厅靳不许。复携家至北京,张艳帜于云吉班。凤仙性慧,款接间,时从诸文士执经问字,久之遂能通大义,阅书报,翩然闺阁名媛也。 李定夷文说: 京妓小凤仙者,杭产也。其父亲任前清武职,以案褫职,家道中落,乃携妻女至沪,市果饼以为生活。旋以食指太多,质女入乐籍。又因女尚年稚,为捕房干涉,禁止营业。遂举家北上,仍张艳帜,名小凤仙。凤仙貌殊美,面作瓜子形,容光白润,态度轻盈,临风玉立,遥望若仙,且工谈吐,精戏曲,解史书。 戒甫文说: 小凤仙,杭产也……据谓(其父)曾任有清武职,以家道中落,携妻女鬻饼沪上,旋质女妓籍。已而,凤仙年过幼,见逐于英捕,遂举家北上。初至,客寥寥……凤仙面作瓜子形,色纯白,体态轻盈,远望若仙子。惜上颚左右有二牙外露,开口颇损美观。然近询之自京来者,则云已易金牙矣。又谓凤仙去岁眷于蔡公,名始大噪,盖其时年已二八,玉立翩翩,且工谈吐,精戏曲,解书史。 以上三文发表的时间,分别为:张相文之文,年“冬月”(即农历十一月);李定夷文,年7月;戒甫文,年11月12日。发表最早的恰恰不是张相文一文,而是戒甫之文。可见,说张文发表“最早”是没有根据的,以此作为评判张文可信的理由自然不能成立。由此也说明研究历史,必须充分占有史料,否则,即如张相文《小凤仙传》是否“最早”问世这样一个小小的结论也要出纰漏。综观三文内容,不仅意思基本相同,连文字表述也大同小异,其陈陈相因的关系,一目了然。唯一不同的是谭、张两文对小凤仙父亲如何“落职”未作交待,而李文却添油加醋,说是“以案褫职”,至于因何案而“褫职”则不得而知。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三文均无只字提及或透露小凤仙的父亲是“旗籍”,陈旭麓仅依据曾虚白后来撰写的《曾孟朴年谱》中的说法,便断定小凤仙为杭州“旗籍”武官的女儿,似有存疑的必要。 作者治学严谨,又是否能成为判断史料可信的条件呢?也须具体分析。一般说来,治学严谨之作,就像名牌产品一样,易让人放心。但严谨作者也只是不会有“造假”的故意而已,毕竟还要受到个人治学时间、精力、情感、环境等等外部条件的影响,因此,出现某些不依作者意志为转移的偏差也并非不可能。就张相文《小凤仙传》而言,除有关小凤仙的身世外,个人以为绝大部分内容都不能轻信(详见下文)。至于说《曾孟朴年谱》因其作者为“孟朴公之哲嗣,子写父传,应不会作假”,则更有讨论余地。为贤者讳,是中国修史的传统,“家丑不可外扬”,至今仍相当有市场,子写父传,就一定不会作假?曾虚白写他的父亲如何对后来名声在外的小凤仙施救,乃是一桩好事、善事,当然不可能隐而不书,但夸大其词则未必不可能。所谓蔡锷对小凤仙有“金屋之议,因小凤仙不易就范,始终没有办法”,蔡知曾孟朴“跟小凤仙夙有渊源,因设法与先生交,以撮合的重任相托,卒经先生从中劝解,成立了这段英雄美人的撮合,也可说是千古佳话了”。个人以为就是十足的杜撰(详见下文),全然不可信。 这么说来,张相文所述小凤仙的身世,是否意味着不可信呢?倒也不是,只是在辨析方法上存在缺陷而已。其实,张相文所述小凤仙的身世还是相当可信的。因为,第一,不是他杜撰的,有其史料依据,而且来源于堪称发表“最早”的《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一文;第二,事实证明,《蔡公松坡之轶事四则》的记述多数还是比较可信的。 首先,从文中所介绍的蔡锷的处事待人方式看,这位自署“戒甫”的作者似对蔡锷比较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iuhuanga.com/nhjb/8521.html
- 上一篇文章: 掰车丨马自达3昂科塞拉VS本田思域老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