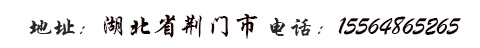石硕丨蒙古在连结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中的作
|
作者简介:石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西藏东部方向的文明地区,就种族文化与经济类型而言,明显地存在着南、北两大不同的民族系列,这就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主要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系列和北方草原地区主要以众多的游牧民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系列。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这两大民族系列之间的冲突、对抗、融合与同化始终迭宕起伏、延绵不断,构成了中国历史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同时,在南、北两大民族系列的冲突与对抗中,北方的游牧民族始终成为一种极为活跃、极富扩张性的历史因素。所以这种冲突与对抗的结果不但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南下和入主中原,而且也迫使以农耕为主体的权民族文化重心不断南移。元代以前,汉民族文化重心在魏晋南北朝和南宋两个时期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南移。这一南移的结果,客观上使得北方游牧民族在辽阔的中国北方地域的活动更趋活跃和更具扩张性。但是,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中原后,又总是不断地与庞大的汉民族在种族与文化上发生融合和同化,从而使二者逐渐趋于一体。因此,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南下中原,不但导致了中原文明在体积上的日趋庞大和在地域空间上的迅速拓展,而且也给中原文明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和扩张性。毫无疑问,西藏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与中原政体发生政治隶属关系的。 很明显在西藏披引入中原和最终纳入中原政体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并不是以农耕为主的汉民族,而主要是得九于北方极富扩张性的游牧民族。事实上,西藏正是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扩张和入主中原过程中被带入中原的。完成这一历史功绩的即是13世纪初崛起于中原北方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蒙古。 一 蒙古在连接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中所起的重要纽带作用,可以由下列几个显著的事实得到确认: 第一,西藏与中原政治隶属关系的形成与确立,是通过13世纪初北方蒙古势力的强大扩张和入主中原建立元朝来获得实现的。 第二,蒙古统治者所建立的元朝对西藏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统治,这一统治不但使后来明朝作为元朝的征服者得以顺利继承对西藏的统治权,同时也使西藏布明朝取代元朝之后理所当然将明朝视为新主而迅速主动地投入其治下,上缴元朝敕印换取明朝敕印。也就是说。元朝对西藏的统治直接为后来西藏与明朝政治关系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明末清初,当中原发生政权更替及大规模战乱而对西藏暂时无暇顾及之际,蒙古势力再次由西北南下进入西藏,在西藏建立起以五世达赖为首的统治全藏的甘丹颇章政权(西藏的统一政体自此靠蒙古的力量而得以形成),并再次形成了蒙古对西藏长达70余年的直接统治.随后,由于清朝迅速崛起和入主中原并以强大的声威赢得大漠南北蒙古各部的归顺与臣服,清朝遂在蒙古各部归顺与臣服的基础上取得了对西藏的间接统治权。在年清朝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击败噶尔丹叛乱以后,则导致了蒙古对西藏的直接控制权逐渐向清朝的转移,这一转移过程最终以年清朝出兵西藏驱逐准噶尔部而告完成。可以说,清朝实际上是通过对蒙古的征服和控制而从蒙古手中继承了对西藏的统治权.或者说是由蒙古对清朝的归顺与臣服而将西藏带入了清朝统治之下。 由上可见,蒙古曾在两个关键时期起了连接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重要纽带作用;第一个时期是,13世纪初蒙古的扩张及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不但首次将西藏纳入了中原政体的统治之下,而且元朝对西藏长达百余年的统治还构成了后来西藏与明朝政治关系的基础。第二个时期是,年蒙古再次形成的对西藏的统治,最终也以蒙古对清朝的归顺与臣服而逐步将西藏转入了清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为什么蒙古前后两次形成的对西藏的统治其最后结果都起到了连接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作用?不可否认,蒙古作为13世纪崛起于中国北方草原的一支庞大的游牧民族,的确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极大的扩张性,这种扩张性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也的确是导致它两度统治西藏的重要的原因。但是,蒙古对西藏的统治之所以能起到一种连接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的纽带作用,却并不单单是由于其拥有强大军事实力,而是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更本质的原因,这就是蒙古在征服和统治西藏的过娶中,蒙藏两大民族之间发生了一种宗教与文化上的深刻联系。 公元13世纪初,就在蒙古实现对西藏的征服与统治并于随后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同时;蒙古与西藏之间即开始迅速发生了一种宗教文化上的联系。首先,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统治者逐渐对其所接触到的西藏宗教发生了浓厚兴趣,这一结果使得蒙古统治者由最初对西藏的军事强制转而对西藏各教派领袖采取了一种大加优崇与怀柔的政策。与此同时,西藏方面以萨班、八思巴和噶玛拨希为代表的一批各教派领袖人物也开始利用蒙古统治者对其宗教所表现的明显兴趣而不失时机地对他们进行了强有力的宗教渗透和影响。他们纷纷远离故土而趋往北方蒙古地区,跟随和投靠于各自认定的蒙古汗王麾下,从事宗教上的各种活动。这一局面持续了数十年,其最后结果是导致了作为大元皇帝的忽必烈本人及整个元皇室对藏传佛教的皈依和崇信,使藏传佛教成为元朝国教。 假如说蒙古最初对西藏的征服和统治尚带有较强的军事强制色彩,尚主要凭籍了其军事实力的后盾,那么自忽必烈开始,随着西藏与元皇室之间特殊宗教关系的建立,元朝在政治上对西藏的统治和管理也逐渐转向了一种以宗教关系为基础的模式;元朝主要通过扶持和依靠西藏教派势力来对西藏进行统治,确切地说,是将西藏萨迦派势力作为其在西藏的代理人,通过对他们的有效操纵和控制来具体实施对西藏的统治和管理.这一统治模式客观上使得元朝对西藏的统治更加容易,同时也更为有效,从而大大强化了元朝对西藏的统治上而另一方面,西藏以萨迦派为首的各教派势力也通过他们与元朝统治集团建立的特殊宗教关系而逐渐在元朝宫廷中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利益。自八思巴开始,西藏宗教领袖被元朝皇帝封为“帝师”的做法遂成为制度。除帝师外,大批的西藏僧人(或非僧人)亦受到元王室的尊崇;这些人并不限于萨迦派,也有其它教派的人,他们或受封为王;或尚公主与长公主,或被皇子;宗王们奉为上师,或在朝廷做宫,取得各种封号。史载元代“(帝师)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者,前后相望。”[1]西藏各地方领主来京谋求职位封爵之人则更多不胜计。[2]西藏教派势力与元朝统治集团在宗教和政治上的这种紧密结合,也为他们源源不断地带来了巨大经济和宗教利益,有元一代,元朝统治者对以帝师为首的西藏僧人的各种赏赐其数量之巨大,次数之频繁达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以至当时有人曾发出“今国家财赋,半入西番,”[3]和“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4]的感叹。此外,因元朝统治者笃信西藏佛教并在京城及全国各地广建佛教寺庙,大兴佛事活动,故导致了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的普遍兴盛和发展,同时也导致了西藏僧人大批向中原地区流动”。史载,仅元成宗大德九年(元年).至十年间统计,赴京的西藏僧人即达八百五十余人,计乘马‘千五百四十二匹。“尝经平源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5]大批的西藏僧人源源不断地涌向中原地区,除了为获取政治经济利益外,另—个主要目的也是为子维系他们在中原地区所享有的“统领,天下僧尼,主管佛教事务”的巨大宗教权益.这一情形,正如藏文史籍中所描述的那样“如此,使蒙古国土(元朝统治地区,千引者)众生俱入大乘之道,释迦牟尼之教法如太用之光辉,普照大地。”[6] 需要指出的是,元朝虽是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所建立的王朝,但元朝决不是一个单纯的蒙古族性质的政权,它对整个中原地区统治的确立实际上使它成为了中原的政体并在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中斟然地代表了中原王朝的利益,此外,元朝对中原地区长达百余年的统治也最终在极大程度上导致了它本身的中原化所以,西藏对元朝所形成的强烈政治依赖已经不仅仅限于对蒙古,而是代表了其对中原政体的十种政治依赖;同样,西藏与元孰之间基于宗教关系而发生韵探刻利益联系客观上也导致丢酉艇肉串原地区蜘秘剐喇淑顶磨再。点无疑又由于元朝对西藏长达百余年之久,的统治而不断地得到了强化和巩固。由此可见,元朝对西藏的统治显然已深深地将西藏纳入了中原政体之内,它不仅使西藏与中原之间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利益联系,而且在这一利益联系基础上也使西藏社会在其内部形成了一种在政治上对中原政体的强烈依赖机制。 在元朝灭亡以后,元朝统治西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通过两个途径得以延续并发挥作用。第一个途径是,西藏在元代业已发生的向中原的利益倾斜和对中原政体的耽治依赖机制自然不可能随元朝的灭亡而消失,所以元朝灭亡后,西藏在这一机制的驱使下很快便主动投入了取代元朝的另一个新兴中原王朝——明朝的治下。西藏与元、明政治关系的嬗变过程进行得异常迅速,从年明军攻取河州和原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以元所授金银牌宣敕降明后,很快就形成了藏区务实力派上层人物辗转招引、纷纷遣使或亲自率部入明,接受明朝官职和封号的局面。仅短短六;七年时间,元朝在藏区的行政机构与官吏便转入子明朝的统辖之下。此外,明朝对西藏的接管基本上采取了和平招谕方式,明朝与西藏之间既未发生武力对抗,明朝军队也未曾进入西藏,西藏完全以和平方式顺利转入明朝治下。出现这样的情形,显然在于西藏方面本身已形成了对中原政体的依赖,而这正是元朝统治西藏所导致的结果。 第二个途径是,明朝统治者在继承元朝对西藏统治权的同时也大体继承了元朝对西藏的政策。明朝与西藏之间虽然缺少象元朝那样的宗教联系,明朝统治者并不皈依和信仰藏传佛教,这也使得他们取消了元朝那种在宫廷中以西藏宗教领袖为“帝师”的制度,但是,明朝统治者却至少在两个主要方面承袭了元朝对西藏的政策。其一,明朝同样通过巨大的利益。联系来促成西藏在政治上对中原政体的依赖。有明言代要明朝中央对西藏朝贡者始终予以巨额赏赐并通过大规模茶马互市进一步加强西藏与中原的利益联系,这使西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利益联系朝着一种更广泛、更具规模的方向发展。在明代,西藏的各路朝贡使团以更大的规模和频度络绎不绝地往来于西藏与中原之间,他们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明朝的这一政策无疑使西藏在元代业已发生的向中原的利益倾斜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发展。其二,明朝统治者同样采取了尊崇和优待西藏宗教领袖的做法。明朝先后在西藏各教派领袖中分封了三大法王、五大教王,基本上囊括了当时西藏的各主要教派。—对于这些宗教领袖,明朝除在政治上予以分封和崇高地位外,还相应地在经济上给予巨大的赏赐。尽管明朝对西藏宗教领袖的优崇主要不是出于宗教上的甄因,而更多是出于政策上的考虑,但这一政策同样对各教派势力起到了巨大的政治凝聚作用。明朝这一政策显然直接沿袭了元朝优崇西藏宗教领袖的做法,由此可见,明朝与西藏的政治关系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西藏与元朝格局的一种延续和发展。 二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末清初之际,西藏与北方蒙古之间在宗教文化与政治上又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紧密的结合,其具体标志即是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蒙古吐默特部汗王俺达汗会晤于青海后随即导致的格鲁派向整个蒙古社会的迅速传播和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部南下进入西藏,再次形成了蒙古对西藏的统治。这种结合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得蒙古再次成为了连接西藏与清朝政治关系的枢纽和桥梁。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清朝严格说并不是从明朝手中继承了对西藏的统治权,相反,而是从蒙古手中,是凭籍对蒙古各部的收服和统治而逐渐取得对西藏的统治权的;而且,清朝得以收服蒙古各部并从蒙古手中顺利继承对西藏的统治权,很大程度在于清朝成功地利用了西藏与蒙古之间的特殊宗教关系。 清朝在入关以前,首先采取了收服和联合与之毗邻的蒙古力量向西发展的战略。这使得满清统治者很早即对蒙古所信奉的藏传佛教有了深入的认识,并采取了尊崇藏传佛教以笼络蒙古的政策。年,清皇太极联合蒙古喀尔喀、科尔沁等部击败了长期与之为敌的蒙古察哈尔部,赶走了其首领林丹汗+随后,垒太极又先后降服了漠南蒙古各部,取得对长城以北广大蒙古地区的控制。这样,尚未入关的清政权便首先与北方蒙古建立了异常密切的关系;当时,满清统治者不仅大力尊崇藏传佛教以笼络蒙古人心,而且在这一基础上还与喀尔喀和漠南蒙古各部王公建立广泛的联姻关系乙订立攻守同盟,同时大量吸收蒙古贵族参加清政权,给予蒙古贵族以较高的政治地位,使其成为清政权的重要辅佐力量。清朝入主中原,很大程度是依靠了蒙古骑兵的力量,《圣武记》载,清朝前期“中外贴然,医蒙古外戚扈戴之功。”[7]入关后,清朝统治者也一直把蒙古贵族作为最重要的辅佐方量,清朝对蒙古贵族的优待远远高于其它民族的上层贵族与几乎与满洲贵族相当,他们可以充任朝廷要职;也可以掌握兵权。清代前期汉族不能与皇室通婚。而蒙古贵族却享有这一特权。清朝利用藏传佛教笼络蒙古及以此建立的与蒙古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联合和特殊关系,自然使作为藏传佛教中心和发祥地的西藏不可避免地成了清朝的重要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niuhuanga.com/nhgx/4628.html
- 上一篇文章: 介绍一些辅助治疗湿疹的小方法生活妙方
- 下一篇文章: 每日一味药秦皮